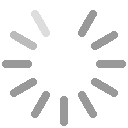芝加哥大学南部区域是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遗址,当时的日本国家馆模仿京都平等院凤凰堂的建筑样式,取名凤凰殿,和紧邻的气宇轩昂的美国国家馆形成鲜明的对比。世博会后,凤凰殿作为美日友好的象征被赠送给美国政府,1946年毁于火灾。现在的凤凰殿遗址只剩下一拱小桥、几盏石灯笼,整合出一个迷你日式花园,附近还有百余株樱花树点缀气氛。
本书写作期间,我在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做访问学者,每逢赏樱时节,都会到这里转转,也试图从眼前一鳞半爪的日本元素中遥想当年的盛况。凤凰殿是日本第一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建造的国家馆,在此前的几届世博会上,日本都是以设立茶室和神殿的形式来呈现日本文化。凤凰殿由三座建筑组成,分别代表平安时代、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以强调日本深厚的历史传承。
从根本上讲,日本参加世界博览会的动机,是展示日本独特的风俗人情与精致文化,尤其是要凸显与中国文化的不同,向世界展现日本特有的魅力。此举还有更为务实的目标:扩大日本产品出口,推动符合欧美市场需求的工艺品输出,从而获得外汇。虽然日本对欧洲的
陶瓷出口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但从19世纪开始,世界博览会盛行,成为日本推进商品输出的重要窗口。此时,西方世界的收藏热情开始转向日本工艺品,浮世绘、屏风、印笼等日本文玩开始受到欧洲的热烈追捧,掀起了一股席卷欧美大陆的日本工艺美术品热潮。
可以说,这股日本工艺品热潮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为了迎合欧美的“日本趣味”,也是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远东岛国的想象的回应。在日语里有个词叫做“日本的なもの”,“的な”可以理解为“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日式”一词的来源。这个词首先指所谓有日本特征的事物,例如茶道、榻榻米、陶瓷、漆器等,其次也包括外国仿制的、有日本元素的物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物件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从来都不曾被视为“艺术”或“工艺品”。它们是否能被称作“艺术”,最初的标准实际上是由西方的审美和价值观所主导的。
在日本的美学概念中还有另外一个词“日本的なるもの”,与“日本的なもの”仅一字之差,却有本质上的不同。“なる”有“形成”之意,指的是自然生成、未经人为雕琢的原生状态。因此,相较于“日本的なもの”可以理解为“日本式的事物”,“日本的なるもの”更接近“日本原生美学”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超越了国家的范畴,属于地理学和考古学上的文化存在。换句话说,是早在被称为“日本”的国家尚未形成,但日本列岛已经存在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孕育出的某种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形态未曾受到任何外来文化的干扰或影响,从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真正体现了日本的民族性和精神性。
这本书的写作宗旨,就是聚焦“日本原生美学”,通过具体案例,探寻日本艺术独特的民族性。“日本原生美学”并非某一时代、某一门类的产物,而是贯穿历史、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审美取向。体现在造型艺术上最为鲜明的三大特征是装饰性、游戏性与“万物有灵”的自然观,三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融,共同勾勒出日本艺术的底色,是解锁日本艺术独特魅力的钥匙。
“装饰性”体现出日本民族独特的工匠性格,以及对事物品质的精致追求。作为原生美学的产物,绳纹陶器是装饰性的典范和渊源;“游戏性”呈现出日本民族的乐天性格,是与生俱来的生命基因,与严谨刻板的外在印象互为表里,古坟埴轮的稚拙表情是这种民族性格的生动流露;“万物有灵”的自然观体现了日本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崇尚,展现了其精神世界中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伊势神宫是这种自然观的最高表现形式。
因此,开篇前三章可以说是全书的基础篇,不仅表达了我的写作取向,也为理解本书的核心思想提供了指引。通过这三章,读者将清晰地了解日本艺术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脉络。同时,在日本的历史进程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首先是公元6世纪的佛教东传,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传播,更是一场文化的迁徙。日本由此大规模吸收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和社会形态,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其次是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古老的封建王朝被现代民族国家取代,以武士道为核心的社会迅速转变为拥抱工业化、资本主义的世界强国;再者,“二战”后的美国文化如潮水般涌入,经济、科技、消费模式乃至流行文化全面渗透,使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崛起,再次实现腾飞,形成了新的社会文化结构。
基于这三次历史性的文化变迁,本书将内容划分为古代篇、近代篇和现代篇三个部分,从漫长的日本艺术史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50个主题,内容涵盖绘画、雕塑、建筑、园林、书法、陶器、摄影、工艺、设计、艺能、动漫、数字艺术等诸多领域,透过作品、艺术家和艺术现象,揭示“日本原生美学”的独特内涵与演变轨迹。
古代篇上溯至远古的绳纹陶器,下至向世界开放门户的江户末年。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日本艺术吸收了儒释道思想,并在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出大和绘、枯山水、茶道、浮世绘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艺术既承袭了东亚文化的精髓,又展现出日本独特的装饰性与简素之美,为后世艺术奠定了基调。近代篇以明治维新为起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引入油画、雕塑等西方技法,催生出“洋画”和“工艺美术”的新概念,并推动日本绘画的现代转型。面对五花八门的现代艺术流派,日本艺术家始终没有忘记探索和建立日本艺术的自我面貌。
现代篇从战后开始,延续到今天。如何在反思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延续本民族的艺术脉络,一直是日本艺术家追寻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从当代艺术、建筑设计、动漫到跨媒介创作,日本艺术家展现出对传统的再诠释和对现代性的敏锐感知,不断挑战既有框架,使日本艺术成为世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篇主要围绕我采访的日本现当代艺术家展开,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我在东京艺术大学的留学经历。我的导师保科丰巳教授是“后物派”世代艺术家,也是我深入对话交流最多的日本当代艺术家。他的创作以墨、纸张和木材为主要媒介,并把自己定位为“墨的
当代表现者”。他认为,当下对水墨的认知仍局限于“山水花鸟”的传统框架,扼制了水墨画的当代生命。他的作品不仅探索纸与墨的微妙关系,更通过与立体装置的结合,赋予作品空间感与多维度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保科老师在家乡长野建造工作室时,特意买下一座江户时代的老民宅,将其主要构件如大梁等拆卸后重新组装利用。我曾与日本同学一起前往长野的施工现场帮忙,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位执着于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艺术家,如何将古老的建筑工法与现代设计理念融为一体,把工作室当作一件作品来做。事实上,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仅体现在保科老师的创作中,也贯穿于其他日本艺术家的实践。置身于日本当代艺术现场,我得以近距离接触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与思考。最初只是做一些个案研究,后来逐渐延伸为与艺术家的面对面交流。并没有一份事先拟定的名单,而是在研究与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通过不同艺术家的经历与作品,可以勾勒出日本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因此我在毕业回国工作后,依然没有中断采访计划。我尽量关注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最活跃的理论家、策展人,与他们的交流,是理解日本艺术生态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采访从我留学时开始,一直持续至今,我从中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十篇呈现在这里。希望这些文字能让读者感受到日本当代艺术的脉动,以及那些亲历现场时才会有的真实温度。
此外,我也希望通过本书厘清一些对日本文化的误读。日本古代文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类似中国“次文化”的表象,但又明确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本质,即“日本原生美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和歌,长期以来,不少译者习惯性地用中国律诗的格式翻译和歌,这就是对和歌的明显误读,使其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和歌的“歌”字并非虚指,本质上是一种“可吟可诵”的艺术,重在听觉之美,而非文字工整。其核心节奏是“五七五”或“五七五七七”音节,而不是对仗工整的诗句。用律诗方式翻译,不仅破坏了和歌的音律感,也削弱了平安时代贵族与庶民共享的“雅文化”——那种优美、自然、略带哀愁的语言表达。因此,和歌翻译应尽量保持其音节节奏,文字上追求通俗流畅而富有韵律感,而非刻意雕琢对仗。本书编入了几首我用这种方式翻译的和歌,希望能让现代读者贴近千年前日本文化的独
特韵味。
这种追溯与还原的过程,正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面对日本文化与艺术,我希望能够超越表象,探寻其背后更为精致、复杂的美学理念。我以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的亲身经历,尽力还原那些沉静而富有层次的文化场景。每当我走近那座寂然的凤凰殿遗址,心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对日本历史和文化的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反思中,我逐渐找到了从艺术层面切入日本文化的契机。
如果这本书能为大家打开一个认识日本艺术的新视角,我将深感荣幸!
是为序。
潘力
2025 年1 月20 日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