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华,江苏无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育研究专家、中国科学计量学创始人。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64-1970)。 现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兼科普翻译委员会副主任。 2021年7月19日 中国行为法学会聘为“国家与地方治理委员会”高级顾问。 主要涉足专业领域: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教育信息化、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创新、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大学科研评价与大学排行榜研究、教育产业的理论与政策,以及城市科学。 获奖及荣誉 :2022年4月24日,荣获科学计量学《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计量学家》称号,在第十三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上,由《邱均平计量学奖》评审委员会和全国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授予。 2022年12月25日,研究会学术年会上,荣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授予《终身成就学者》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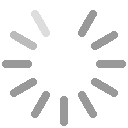
科学学的历程
-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 下载次数:1802
- 书籍类型:Epub+Txt+pdf+mobi
- 创建日期:2024-10-01 07:10:02
- 发布日期:2025-09-15
- 连载状态:全集
- 书籍作者:蒋国华
- 运行环境:pc/安卓/iPhone/iPad/Kindle/平板
- 下载地址
内容简介
《科学学的历程》从科学学的最早起源事件和发展谈起,详细记录了整个科学学初期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对科学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并对笔者在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回顾。全书以科学学为主线,既回顾了历史,也讨论了实践。既是对科学学的历程的回顾,也是对个人所经历的科学学的历程的反思。本书可作为科学学、科学计量学以及科技政策等相关研究者和高年级学生的辅助读物。
全书共6篇33章。第一篇,科学学的起源;第二篇,科学学的思考与探索;第三篇,政治课学学与科学基金;第四篇,科学计量学的起源;第五篇,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第六篇,赵红洲与中国科学学。
作者简介
下载地址
序言
前言
际此旧作《科学学的起源》本书是《科学学的起源》(2001)的再版,其中对原书的结构和内容做了很大的调整,并在李杰博士的建议下,命名为《科学学的历程》。盛情受邀再版,收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科学计量与知识图谱丛书”,该丛书主编李杰博士更热情地建议把书名改为《科学学的历程》,并建议增添了上次出版后的若干新著,我是举双手赞同的。李白诗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斯言信夫。李博士青春年少,才情俱佳,建议把“起源”二字改成“历程”后,立马感觉天高地阔了。兹循着李博士建议变更的“历程”二字,简要地讲一讲我的科学学历程,同时,借以表达对红州恩师的追忆和怀念,某种意义上,亦不失是对我国科学学创始人之一的张碧晖教授念兹在兹的中国科学学发展史研究,特别是早期史料的一点补充。
我的科学学历程
宋代理学大师、湖湘学派创立者胡宏有句名言,“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我的科学学历程的“源”和“根”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我的恩师赵红州教授,是他把我引上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次改变我一生学术研究路径的谈话。
那是1978年的春末夏初。于光远亲率龚育之、何祚庥、查汝强、李宝恒、罗劲柏诸导师,组成导师组,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招收10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据刘二中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庆纪念册(1978—2023)》中的回忆文章,当年实际招收了14名参见刘二中:《老文件引发的回忆——自然辩证法教学部意气风发的十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庆纪念册(1978—2023)。)。大约是一个下午,地点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十三研究室,亦即引力波实验室。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出来,据说还不错,红州告诉我,据他了解,我的总分排第三名,外语(俄语)成绩在是年中国科学院考研系统全国第一名。虽然顺利进入了复试,然而,遗憾的是,复试放榜结果我还是名落孙山了。据说,理由是政审不合格。当此之时,红州像兄长大哥般,一边安慰和鼓励,一边径直问:“跟我一起搞科学学,怎么样?”尽管那时我第一次听说还有“科学学”这么一门学问,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蒋国华红州创新精神是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纪念恩师红州逝世20周年[J]科学学研究,2017,35(12):1767-1772
自此之后,我们俩虽不能说形影不离,但每周见一次是必须的,有时几乎是三天两头都会见面。其时,红州家住沙滩北街甲2号,红旗杂志社职工宿舍,原是一个2居室,分配给了两家住,合用一个很小的厨房。我家住朝阳门北顺城街79号大杂院里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般家里没有资格装电话,不远,三四站路,骑车一刻多钟的路程。毛主席说过,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要交流只有迈开两条腿,登门求教,恰似我国数学泰斗华罗庚先生终身座右铭表述的那样:“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学术谈几声”华罗庚的数学之路,2021年10月20日。
红州在决定接受我这个学徒之初,也是经历了一番测试的。头几次见面聊天,看似海阔天空,实则是考察我的科学素养、哲学功底,文字能力,翻译水平,当然还包括待人接物等,用现今的语言讲,就是品格与情商。比如,有一次我们几乎就唐诗宋词谈了大半天,颇有投缘之感。我回家便学汤显祖《牡丹亭》集唐人诗句的写法给红州凑了一首“诗”,以表心迹:
东风渐暖满城春(张藉),
与君相见即相亲(王维);
若许移家相近住(白居易),
看吐高花万万层(韩愈)。
“面试”通过之后,红州是这样带我开始我们/我的科学学历程的:
第一,带我参加科学学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学术组织。
追随红州学习科学学研究,基本上就是践行了毛主席的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36:174我的印象中,他没有给我专门讲过科学学的入门课,不过,凡是邀请他出席的所有科学学的活动,红州都让我跟着他去,包括外地讲课。这使我赢得了中国科学学诞生和发展史上多个“第一”——第一批参与者的名声,诸如,“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1979)、全国第一个科学学联络组织——“中国科学院科学学全国联络组”(1979)、全国第一个科学学研究机构——“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科学学研究组”(1979)、全国首届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学术研讨会(1980)、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1982)、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1982)等等。
作为我国科学学诞生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兹附上几幅文献照片和科学学研究组名单(参见图1)。
图1我国科学学诞生的重要历史文件“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科学学研究组”于1979年7月21日正式成立,举办单位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霍俊教授为会长的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组长:霍俊;
副组长:王兴成、李秀果、杨沛庭、金良浚、周文森;
组员:骆茹敏、赵红州、徐耀宗、符志良、贾新民、王敏慧、李秀果、李惠国、王兴成、范岱年、郑慕琦、韩秉成、丁元煦、杨沛庭、柴本良、霍俊、金良浚、崔佑铣、胡乐真、蔡文煦、曹听生、周文森、冯至诚、雷祯孝、王通讯、朱新民、邸鸿勋、许立达、王士德、蒋国华、李汉林、刘仲春、桂树声、任亚玲、刘泽芬、莫惠芳、李连馥、段合珊、李延高。
第二,带我阅读/翻译科学学经典名著。
红州没有给我开过该读的书单,但在我日常工作交流中,他常常引证经典名著和权威学者的观点,恰如信手拈来,着实令人感佩不已,于是,我遂悟到,真要把科学学作为毕生研究领域,就要像红州那样,需要学习和提升,在诸如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史、科学哲学、管理科学、科技政策研究等理论功底上狠下功夫。
鉴于改革开放之初,除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1982)、《历史上的科学》(1959)及《科学学译文集》(1981)外,可以说,有关科学学的译著非常之少。红州开始让我阅读和翻译俄文的科学学文献,诸如凯德洛夫、米库林斯基等的论文和著作,后来则是英文文献,比如,我俩硬着头皮翻译了为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而结集出版的、科学学经典文献《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该译著1985年6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科学出版社1984—1985年度优秀图书奖。
第三,带我拜访科学家名师。
红州有一句口头禅:“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的几年里,红州总是用这句话鼓励我跟着他,远些的坐公交车,近些的骑自行车,去拜访大家、大学者。诸如,去礼士胡同拜见过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教授,借全国哲学会议之际去友谊宾馆拜访过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借中国物理学会研讨会议,去京西宾馆拜见过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金属和晶体材料学家、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冯端先生。尤其值得多说几句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著名科学哲学家纪树立研究员(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翻译者),有次他来京赴会,会后他住在当时还是偏远的他姐姐家里。好像是那时的公交非常不便,我们是骑车去的,从北沙滩过去,骑了有一小时。红州大约为激励我追寻科学应该不畏难,记得那时他是第一次对我说“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这句话。顺便说一句,本书的核心部分的第一章“科学学的历史源流”,就是在席泽宗院士主动送给我们的格雷厄姆的文章“盖森的社会政治根源: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的基础上Graham L RThe socio-political roots of Boris Hessen:Soviet Marx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85,15(4):705-722,经拓展和研究而写成的。
第四,带我学做大科学家的秘书工作。
为了锻炼我的笔头,红州还经常尽可能地给我“揽活”——为大科学家和老领导整理录音和撰写讲话稿。当然,按我俩的文字惯例,都要经红州阅改和审定后才能交差。不要小看了这一点,正是这样的文字交流,使我受益匪浅,且是受益终身,不仅学习和领悟了红州的学术思想,而且极大而又极快地提升了我的文字能力。到后来,我俩发表的文章连我们的亲朋挚友都猜不准谁是起草者赵红州、蒋国华在科学的交叉处探索科学——从科学学到科学计量学[M]红旗出版社,2002:671。
众所周知,这既是一件费时费力又费智力的“苦差事”,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向大科学家学习和历练自己的宝贵机会。兹举其要者,以资参阅。
第一次接受任务是198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学学联络组”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上,我国原子弹之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到会做了阐述他科学学思想的专题报告。由于其时,三强同志大病初愈,语言表达不甚连贯,事先没有讲稿,又非常重要,必须成文发表,怎么办?红州力荐由我承担录音整理和成文,于是,“全国科学学联络组”负责人之一李秀果研究员几乎手把手地教我:第一步,听录音,一字不落地记下来;第二步,反复读三五遍,完整正确弄懂钱老的思想观点;第三步,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再创作成文。钱老是大科学家,给他的支持新生学科的文章怎么起名呢?我把文章标题空着,红州阅改后说:就用“可算找到老家了”吧!这个标题还引出一个故事呢。钱老审定并赞赏我为他整理得好,随即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82年第1期上钱三强可算找到老家了[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1)。在不久的一次中国科协常委会上,严济慈老先生拿着这本杂志问钱三强:“小钱,这个文章和标题是你写的吗?”在他老师严老面前,三强连声说道:“是的,是的。”
第二次是1980年11月,全国首届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学术研讨会(简称“三学会议”,实际是三个新生学科分别开会)召开。“全国科学学联络组”办公会决定,约请钱三强为全国第二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写个贺信。谁来执笔呢?红州紧接着说:“还是由小蒋来写吧。”千字文不好写,尤其是为饮誉国内外的大科学家写。因为我在贺信的最后一段借用了黄梅戏《天仙配》的一句唱词“天赐良机莫迟疑”,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汪敏熙大姐说:“三强文章从不用文学/戏曲语言的,这么写,不知三强是否同意?”“全国科学学联络组”牵头负责人赵文彦同志则表示同意呈送,由三强自己定夺。
当然,结果非常顺利和圆满,钱老批转同意了。大会作为简报发出后,受到了普遍赞扬,有人还问:“这是谁给钱老起草的呀?真棒!”
第三次录音整理并改写则是最艰巨,工作量也最大。那是1985年4月17日至18日,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堪称“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尤其是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世称“三钱”同台出席,据说在新中国科学史上非常罕见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迎接交叉科学新时代[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会后,红州又为我承接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田夫四位的发言按录音整理成文的任务。记得夜以继日,连续开了几个夜车,终于圆满完成。不久,连同龚育之同志的“从交叉科学看教育改革”,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隆重刊发。为了纪念这次完成任务的成就感,迄今我还保留着我为“三钱”和田夫同志的成文的最后手稿(参见图2)。
第五,带我学习走上讲台,敢于张嘴,敢于独立讲课。
毕竟我1970年毕业离校到工厂,大约10年时间做的是与工人、设备打交道,是技术工作,离学术研究差别甚巨,遑论上台做学术报告了。红州看到了我的这块短板,他时不时鼓励我要敢于面对公众场合,开口讲话。一方面,他以自己曾经怯场的经历缓解我的紧张心理,另一方面,他多次建议我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毛主席说过:“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36:174。
图2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三钱”和田夫发言手稿记得红州第一次“逼”我上讲台是1980年的夏秋之交,中国科协干部管理学院本来慕名请他去做科技管理主题报告的。鉴于对象是全国各地科协机关行政干部的“学经济 学科技 学管理”培训班,属普及性讲座,他就抓住这次机会,推托他有事排不开,便竭力推荐我顶上。还好,初次登讲台,确乎紧张不已,但还算基本应付了下来。紧接着第二次是是年晚些时候,当时的杭州大学盛邀红州做有关科学学的专题报告,他就趁便为我特别申请安排了一个小会场报告,主题是“谈谈科学基金会的引进与建设”。因为那时我俩的论文《论科学基金会》刚刚完稿,尚未发表蒋国华、赵红州论科学基金会,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3:15。虽然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依然记得,讲了2个小时,讲课酬金10元。
再后来,红州还创新了锻炼我讲演能力的合讲模式。1990年1月号,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导报》刊登了我俩的文章“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著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写信给我们,给予这篇文章很高评价,并向同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委员们推荐,说“值得我们看看”。其时,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何文治委员聆听了钱老的讲话,便立马让秘书联系我们,请我们到位于京北小营的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研究院,给航空航天科学家工程师做一场报告。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会,红州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他说:“下面,请我学弟主讲。”最后,他做总结讲话。此次合作演讲非常成功,当场我国的航空航天科学家工程师们非常兴奋,提了好多问题,现场互动交流热烈。
第六,带我学做科学学会议的会务工作。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艺术摘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24。有人循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和逻辑给出了一个推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就是人与人交往不断累积的产物;就是你过去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以及读过的书的总和你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新东方(上海),2017年7月31日。
事实上,一个科学研究者的本质亦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科学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学术社会圈子里人与人交往的渐次累积。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州正是这样指导并为我这个当初还是科学学研究的初学者而争取历练机会的。
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尚未成立之前,我国已举办过两次全国性的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张碧晖等科学学在中国[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43。第一次科学学讨论会是1979年7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那时我还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班。第二次科学学讨论会则是1980年11月在安徽合肥稻香楼宾馆召开的,红州便力荐我代表中国科学院科学学全国联络组,作为会务先遣小组,跟随其时国家科委政策局局长吴明瑜以及邓楠、张登义先一天到达。这一次合肥稻香楼会议,学术界简称为“三学会议”,是后来先后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未来学研究会、中国人才学研究会三个新生交叉学科,在国家科委引导和支持下,联合一起在安徽召开的我国改革开放史上一次重要的交叉科学会议。我既是科学学会议的会务组组长,亦是整个稻香楼“三学会议”会务组成员。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2年6月9日至12日在安徽佛名四海的九华山举行。也是红州建议,中国科学院科学学全国联络组委派我跟随《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任丰平社长,作为会务先遣小组,先飞到合肥,然后,省科委张副主任陪同我们,坐汽车经安庆,摆渡过长江,到九华山。这次会议盛况空前,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70名代表出席,我国著名学者和科技部门领导人童大林、于光远、吴明瑜、龚育之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收到论文168篇。至今思九华,作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亦油然而生一种与有荣焉、幸甚至哉的骄傲。
第七,带我学习做科学的组织者,尊敬、竭诚而又谦卑的为科学学师长、同行、友人服务。
我们写“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那篇文章,乃是与红州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这一个学术观点非常欣赏、认同和思考有关。
卡皮查在1966年写道:“任何新的科研课题的解决,都必须找到它自己适当的组织形式。作为一个大科学的领导者,即使他本人不直接参加科研工作,他也必须是一位具有巨大创造性天才的人。我不知道,像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样辉煌成就的领导者,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奖金?”他还继续写道:“大科学家也就是集团科学劳动的大组织家。比如,罗瑟福和费米,就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科学家。”戈德史密斯,马凯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科学[M]科学出版社,1985:110-111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刘霞高瞻远瞩筑通途——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N]光明日报,2011-06-16。在科教界,特别是年轻学者和新生学科,比如像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等,不要说申请研究课题、出版著作,就是想开个哪怕是小型座谈会、研讨会,报批都是困难重重的。当此之时,红州便带着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习并担负起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活动的组织工作。红州拿大主意,是设计者,我则是助理、帮衬,是施工者。
我们组织的第一件大事,红州称之为“无形学院”。1978年党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整个科技界春潮涌动、思想活跃,一派“逢草逢花报发生”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钱起,春郊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九,钱起四[M]中华书局,1960:2688。“无形学院”名称借自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7月15日正式成立前的史话和爱因斯坦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恰似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定义的“地理上分散的科学家集簇”,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称之为“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群体”转引自:百度文库,。开始只有三五人,后来发展到七八个,有时多至十余人。这个“无形学院”最成功的就是孵化出了科学计量学、政治科学现象/政治科学学、领导科学。
第二件大事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等新生学科的研究同仁,组织出版了两套交叉科学文库/丛书一是“交叉科学文库”,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计13本,分别为:《科学 哲学 社会》(龚育之)、《科学教育与科技进步》(张碧晖)、《科学学与我的工作》(张国玉)、《论智力开发》(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科学学与系统科学》(王兴成)、《现代综合进化论》(卢继传)、《物理学的哲学思考》(柳树滋)、《管理 管理 管理》(何钟秀)、《论战略研究》(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信息的科学》(钟义信)、《科技经济学探索》(胡乐真)、《论科技政策》(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论领导科学》(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
二是“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计8本,分别为:《科学的力量》(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历史沉思》(董光璧)、《对历史的宏观思考》(丁伟志)、《科学史数理分析》(赵红州)、《科学学的起源》(蒋国华)、《科学的精神与价值》(李醒民)、《“三文”文化论》(朱进选)、《生态文化论》(余谋昌)。和一套“毛泽东与科学丛书”“毛泽东与科学丛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共计7本,分别为:《万物皆有道——毛泽东与自然科学》、《自然最和平——毛泽东与科学家》(孔令华、蒋国华)、《管理的哲学——毛泽东与管理科学》、《帅才的理论——毛泽东与领导科学》(超英、瑞英)、《无私玉万家》、《科学和革命》(赵红州)、《学习的社会》(蒋国华、蔡棋瑞)。。要知道,这件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啊!
我记得,红州平日里经常对我提起古人“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另一个就是他非常赞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王云五文库”,即王云五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称“万千新知,兼收并蓄”的“万有文库”。在他的成名作《科学能力学引论》付梓出版之后(参见图3)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M]科学出版社,1984,其时,几乎绝大多数年轻的新生交叉科学研究者都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立名作”(红州偏爱这个名称),于是,我俩商议不知多少回,试图用出版“文库”即团队的力量,去感动出版社。谈来谈去,还是一个“钱”字。为此,我俩便奔赴天津,求助时任天津市纺织研究所所长的张国玉。正是张所长赞助的10万元,并在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冯之浚所长、特派教授张念椿的精心运作下,第一套“交叉科学文库”13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成功出版。
图3恩师红州赠送的《科学能力学引论》为了成功出版,我俩事先与诸位作者取得共识:一是没有稿费,只是给每位作者20本书;二是当然也没有主编/编辑费什么的。光明出版社说纸张紧张,我还跑到541厂(国家印钞厂)去找厂领导帮忙过。当时说没有纸,红州与我急得没有办法,即所谓急来抱佛脚吧!
第二套“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共8本,是1995/1996年我俩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谈妥的,遗憾的是红州没有亲眼看到它的正式出版。
“毛泽东与科学丛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赞助出版,主编是孔令华,副主编李敏,我们则是执行主编,共计7本。
此外,我们还组织编著了《交叉科学词典》姜振环交叉科学词典[M]人民出版社,1990、《政治科学现象》赵红州,蒋国华,李瑞英政治科学现象[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等。比如,特邀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姜振环教授主编的《交叉科学词典》,在其“内容简介”中就写道:“本辞典是在1985年‘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后,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夫、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薛德震以及金春峰、吴学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赵红州、蒋国华倡导发起,在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编委会及撰稿人历经两年多的努力编写成的。”
目录
目录
第一篇科学学的起源
第1章科学学的历史源流
第一节伦敦科学史大会及苏联代表团
第二节盖森论文的内容梗概
第三节盖森论文的历史影响
第四节盖森的学术生涯与其牛顿论文的关系
第五节盖森论文产生的国内背景
第六节盖森论文国际影响的根源分析
第七节“盖森事件”与贝尔纳的科学学思想
第八节“盖森事件”的启示
第2章科学学应当干什么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是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
出发点
第二节贝尔纳论马克思与科学
第三节贝尔纳论科学学
第四节贝尔纳论学科建设
第3章科学学家谈科学学
第4章凯德洛夫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
第一节马克思论未来一门科学
第二节根据马克思的方法,看当代科学的汇流和
统一问题
第三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前景
第四节简短的结论
第二篇科学学的思考与探索
第5章科学学研究会的名称与学科建设
第一节历史的回顾
第二节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6章再谈科学学的学科建设
第7章《科学学》在中国15年
第一节它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第二节它有一笔历史的功绩
第三节它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第四节它还有一点历史的危机
第五节它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8章《科学学》在中国20年
第9章指数规律与知识结晶学
第10章重视科学发明的年龄定律
第三篇政治科学学与科学基金
第11章研究政治科学学
第12章论政治科学现象
第一节政治科学事件
第二节政治科学运动
第三节政治科学建制
第13章科学学能为政治做些什么
第14章论科学基金会
第一节科学基金会:通向国家资助的历史
桥梁
第二节科学基金会的经济本质:资本增殖的
“催化剂”
第三节科学基金会的社会功能:先导、补充、
调节、摇篮
第四节我国科学基金会势在必行
第四篇科学计量学的起源
第15章科学计量学的历史与现状
第16章再论科学计量学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什么是科学计量学
第二节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和成就
第三节科学引文——科学计量单元
第四节加菲尔德的《科学引文索引》
第五节引文计量的应用
第六节布劳温与科学计量学
第17章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的今天和明天
第一节普赖斯后的科学计量学
第二节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日趋成熟
第三节大科学计量学和小科学计量学的
辩证统一
第四节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的未来
第18章浅谈文献计量学
第19章海通博士论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
第一节科学计量学的定义问题
第二节科学学与科学的定量研究
第三节科学结构与科学计量学
第四节科学学计量学向何处去
第20章普赖斯奖获得者论科学计量学和科学学
第21章科学计量学与同行评议
第一节同行评议的由来与当代实践
第二节同行评议并非无懈可击
第三节科学计量学的崛起
第四节科学计量学与同行评议的有机结合
第22章科学计量学与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趋势
第23章影响中国科学计量学发展的若干国际
交往纪事
第五篇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
第24章普赖斯评传
第25章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术贡献述评
第26章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研讨会综述
第27章普赖斯科学计量学奖
第六篇赵红州与中国科学学
第28章赵红州与科学学研究回顾
第29章赵红州与《科学计量学》杂志
第一节布达佩斯的飞鸿
第二节《科学计量学》杂志
第三节布劳温其人
第四节出任科学期刊国际编委的意义
第30章赵红州的《科学能力学引论》
第31章赵红州的《大科学观》
第一节《大科学观》的国际地位
第二节大科学观与当代的两大成果
第32章赵红州是一位有理论勇气的科学家
第33章赵红州科学学的学术历程
短评
产品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