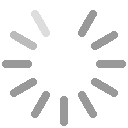
生命不息.归来
-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 下载次数:1984
- 书籍类型:Epub+Txt+pdf+mobi
- 发布日期:2025-09-14
- 连载状态:全集
- 书籍作者:阿特金森
- 图书编号:9787540472917
- 运行环境:pc/安卓/iPhone/iPad/Kindle/平板
- 下载
内容简介
托德家族的男孩子泰迪一直深受父母和姐姐厄苏拉的宠爱,他向往诗意的生活,外出游历,希望能做个游吟诗人。二战爆发,他应召入伍,成为皇家空军王牌飞行员。泰迪数次上战场,驾驶轰炸机九死一生。他本已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然而战争突然结束了,他有了明天,还有明天的明天,可是他的一部分自己再也无法调整去适应未来。内心无限凄惘的他如何才能向明天进发?当生命的多重可能被小心翼翼地捧于手上,究竟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的呢?
编辑推荐
全球畅销小说
100本人生必读书之一
英国科斯塔奖年度长篇 《生命不息》姊妹篇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亚马逊,邦诺书店,BookPage,Goodreads,《西雅图时报》《卫报》《每日电讯报》鼎力推荐
《生命不息.归来》是《生命不息》的相伴之作,是姊妹篇,而不是续集。阿特金森以绝妙的叙事和描绘能力,带领读者在生命的多种可能里探寻人性的真相。本书是阿特金森笔下深刻且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100本人生必读书之一
英国科斯塔奖年度长篇 《生命不息》姊妹篇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亚马逊,邦诺书店,BookPage,Goodreads,《西雅图时报》《卫报》《每日电讯报》鼎力推荐
《生命不息.归来》是《生命不息》的相伴之作,是姊妹篇,而不是续集。阿特金森以绝妙的叙事和描绘能力,带领读者在生命的多种可能里探寻人性的真相。本书是阿特金森笔下深刻且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相关推荐:
生命不息(100本人生必读书之一,2013英美**畅销小说,媲美《偷影子的人》的奇思妙想,超越《返老还童》的情节构思,奥普拉鼎力推荐,《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20多家媒体年度**图书。)
目录
楔子
第一部分
这场战争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裂缝,没有可能回到彼岸,回到他们从前的生活,变回他们曾经的样子。他们是这样,贫穷、破败不堪的整个欧洲亦复如是。
第二部分
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才能活到今晚,都很想知道,命运会不会这么残酷,先让他们活到现在,再把他们置于死地。……“再保佑我们这一次,基督啊,再保佑我们这一次。”
第三部分
在那次出行中,珀蒂了解了外公的一生,也了解了历史,她虽然感到很满足,却也让她对存在的问题产生了不安和迷惑。“答应我,你要好好生活。”他那时对珀蒂说。她办到了吗?没有吧。
《奥古斯都历险记》
后记
致谢
第一部分
这场战争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裂缝,没有可能回到彼岸,回到他们从前的生活,变回他们曾经的样子。他们是这样,贫穷、破败不堪的整个欧洲亦复如是。
第二部分
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才能活到今晚,都很想知道,命运会不会这么残酷,先让他们活到现在,再把他们置于死地。……“再保佑我们这一次,基督啊,再保佑我们这一次。”
第三部分
在那次出行中,珀蒂了解了外公的一生,也了解了历史,她虽然感到很满足,却也让她对存在的问题产生了不安和迷惑。“答应我,你要好好生活。”他那时对珀蒂说。她办到了吗?没有吧。
《奥古斯都历险记》
后记
致谢
作者简介
英国著名畅销小说作家,水石书店年度作者,先后荣获南岸天空艺术文学奖、科斯塔奖,凭借畅销书《生命不息》红遍全球。该书在英美同步上市后,空降各大畅销书榜NO.1,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等20多家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被美国亚马逊编辑评选为“100本人生必读书”之一,也是英国年度畅销小说。
《生命不息.归来》是《生命不息》的相伴之作,是姊妹篇,而不是续集。阿特金森以绝妙的叙事和描绘能力,带领读者在生命的多种可能里探寻人性的真相。本书是阿特金森笔下最深刻且最具想象力的作品。
《生命不息.归来》是《生命不息》的相伴之作,是姊妹篇,而不是续集。阿特金森以绝妙的叙事和描绘能力,带领读者在生命的多种可能里探寻人性的真相。本书是阿特金森笔下最深刻且最具想象力的作品。
下载地址
部分章节
“你现在快乐吗?”南希问,他们两个正在一起刮从树林里采来的冬青与槲寄生的嫩枝。
“是的。”泰迪说,他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方才给出了这个答案,而南希不过是随口问问而已。
枯萎的雪花莲。
“有人觉得采摘这些勇敢的小报春使象征着噩运,所以不会把它们带回屋里。没准儿这是因为它们在教堂墓地里开得格外茂盛。”
希尔维总是会摘下狐狸角的第一株雪花莲。只可惜摘下不久它们就会枯萎死去。
“白色的雪花莲及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质,总是会让这些不起眼儿的小花得到单纯天真的光环。(现在谁还记得上个世纪的少女组合‘雪花莲乐队’?)
“这里讲一个德国传说——”
“噢,老天。”南希轻轻说。
“怎么了?”
“我的钩针掉了。继续吧。”
“这个传说是这样,在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告诉雪去找一些花儿讨些颜色来。除了善良的雪花莲,其余的花都拒绝了,作为回报,雪允许雪花莲在春天第一个开花。
“伟大的音乐具有治愈的力量。德国人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记住德国人的丰富神话、传说和童话,对我们大有好处,更不要说他们的文化遗产了,比如莫扎特的音乐——”
“莫扎特是奥地利人。”
“那是当然。”泰迪说,“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这给忘了。”那就是贝多芬。还有勃拉姆斯、巴赫和舒伯特。舒伯特是德国人吧?
“不是,也是个奥地利人。”
“海顿呢?”他壮着胆子提出了这个名字。
“奥地利人。”
“德国音乐家也不少,是吧?那么,巴赫、勃拉姆斯、贝多芬的文化遗产——”
南希默默地点点头,如同学者确认小学生把错的地方改对了。她本可以去数她那些织针,不搭理他的。
“在这些人之中,贝多芬——”
“我们就像离题太远了。怎么说起德国人来了?”
“因为我写的是一个德国传说。”泰迪说。
“这样就像是在说宽恕德国人似的。你有吗?你原谅他们了?”
他有吗?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是的,可在埋藏真心话的心里,他并没有。他想起了那些他认识的人,他们都死在了德国人的铁蹄下。如同魔鬼与天使,那些死去的人多得已经不计其数。
他自己的战争结束已经三年了。在最后一年里,他丧失了战斗力,被关在波兰边界附近的战俘营里。他的飞机起火了,他跳伞降落,却落到了德国人的地盘上,因为摔伤了膝盖,他被抓了。在那次对纽伦堡的恐怖空袭中,他的飞机被探照灯灯光锁定,进而被高射炮击落。他当时并不清楚,可对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来说,那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一个夜晚,共损失了九十六架飞机,五百四十五人牺牲,比不列颠之战中牺牲的总人数还要多。可等他回到家,那又不过是个过时而冰冷的消息罢了,纽伦堡的那次战役早已不复记忆。“你真勇敢。”南希说,带着几分冷漠的鼓励,反正泰迪听来就是这样的,他觉得要是他在数学考试中得了好成绩,她也会对他说同样的话。
现如今,战争不过是睡梦中一个个混乱且随机的画面,比如月光下的阿尔卑斯山,螺旋桨在空中旋转,水下苍白的脸。那么,祝你们好运。有时是紫丁香花令人烦腻的香气,还有时是在舞曲中甜蜜相拥。这些噩梦到最后总会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在熊熊烈火中,向地面俯冲下去。我们做噩梦的时候,总会在可怕的结局出现前就醒来,不会等到梦到坠落的那一刻,可泰迪只能是在南希的呼唤下才能醒来,需要她摇篮一样的手来抚慰他,他会在黑暗中出神很久,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她在夜里没有叫醒他,会出什么事。
在战争中,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战争突然结束了,他有了明天,还有明天的明天。他的一部分自己再也无法调整去适应未来。
“是的。”泰迪说,他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方才给出了这个答案,而南希不过是随口问问而已。
枯萎的雪花莲。
“有人觉得采摘这些勇敢的小报春使象征着噩运,所以不会把它们带回屋里。没准儿这是因为它们在教堂墓地里开得格外茂盛。”
希尔维总是会摘下狐狸角的第一株雪花莲。只可惜摘下不久它们就会枯萎死去。
“白色的雪花莲及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质,总是会让这些不起眼儿的小花得到单纯天真的光环。(现在谁还记得上个世纪的少女组合‘雪花莲乐队’?)
“这里讲一个德国传说——”
“噢,老天。”南希轻轻说。
“怎么了?”
“我的钩针掉了。继续吧。”
“这个传说是这样,在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告诉雪去找一些花儿讨些颜色来。除了善良的雪花莲,其余的花都拒绝了,作为回报,雪允许雪花莲在春天第一个开花。
“伟大的音乐具有治愈的力量。德国人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记住德国人的丰富神话、传说和童话,对我们大有好处,更不要说他们的文化遗产了,比如莫扎特的音乐——”
“莫扎特是奥地利人。”
“那是当然。”泰迪说,“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这给忘了。”那就是贝多芬。还有勃拉姆斯、巴赫和舒伯特。舒伯特是德国人吧?
“不是,也是个奥地利人。”
“海顿呢?”他壮着胆子提出了这个名字。
“奥地利人。”
“德国音乐家也不少,是吧?那么,巴赫、勃拉姆斯、贝多芬的文化遗产——”
南希默默地点点头,如同学者确认小学生把错的地方改对了。她本可以去数她那些织针,不搭理他的。
“在这些人之中,贝多芬——”
“我们就像离题太远了。怎么说起德国人来了?”
“因为我写的是一个德国传说。”泰迪说。
“这样就像是在说宽恕德国人似的。你有吗?你原谅他们了?”
他有吗?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是的,可在埋藏真心话的心里,他并没有。他想起了那些他认识的人,他们都死在了德国人的铁蹄下。如同魔鬼与天使,那些死去的人多得已经不计其数。
他自己的战争结束已经三年了。在最后一年里,他丧失了战斗力,被关在波兰边界附近的战俘营里。他的飞机起火了,他跳伞降落,却落到了德国人的地盘上,因为摔伤了膝盖,他被抓了。在那次对纽伦堡的恐怖空袭中,他的飞机被探照灯灯光锁定,进而被高射炮击落。他当时并不清楚,可对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来说,那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一个夜晚,共损失了九十六架飞机,五百四十五人牺牲,比不列颠之战中牺牲的总人数还要多。可等他回到家,那又不过是个过时而冰冷的消息罢了,纽伦堡的那次战役早已不复记忆。“你真勇敢。”南希说,带着几分冷漠的鼓励,反正泰迪听来就是这样的,他觉得要是他在数学考试中得了好成绩,她也会对他说同样的话。
现如今,战争不过是睡梦中一个个混乱且随机的画面,比如月光下的阿尔卑斯山,螺旋桨在空中旋转,水下苍白的脸。那么,祝你们好运。有时是紫丁香花令人烦腻的香气,还有时是在舞曲中甜蜜相拥。这些噩梦到最后总会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在熊熊烈火中,向地面俯冲下去。我们做噩梦的时候,总会在可怕的结局出现前就醒来,不会等到梦到坠落的那一刻,可泰迪只能是在南希的呼唤下才能醒来,需要她摇篮一样的手来抚慰他,他会在黑暗中出神很久,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她在夜里没有叫醒他,会出什么事。
在战争中,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战争突然结束了,他有了明天,还有明天的明天。他的一部分自己再也无法调整去适应未来。
……